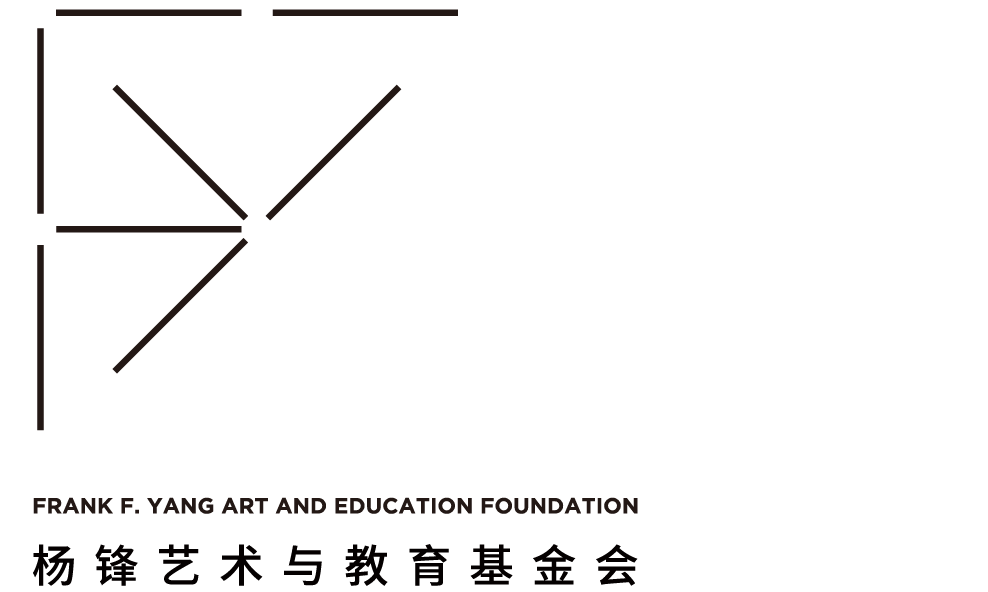大湾区艺术行 | 联结穗深港的48小时位移
新近呈现的日本艺术家田中功起的“不确定任务”中,艺术家邀请人们携带一款可以分享的茶包来到位于广州番禺区的镜花园内,将它们混合冲泡在一起,共同品尝。在敞开的空间情景里,人们受邀成为这个临时共同体的一员。通过阅读、行走和驻留,不同的个体经验交织在一起,进而展开对我们身处何地的思考。我们可以将即将开始的大湾区艺术行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聚集,每年三月在香港举行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作为公共的事件,将人们从世界各地汇集。而短暂48小时内发生的位移,从香港到深圳,从深圳到广州,不单是一次深入了解粤港澳艺术机构的视觉之旅,更像是切身的“城市行走”,将身体经验置身于大湾区这个变动的社会场,以此实现一次对自我的关照和对“他者”的重新认识。
>> 四个机构的个展面貌 <<
OCAT深圳馆和时代美术馆在这个三月都推出了艺术家的阶段性回顾展览,由此看出两个机构在学术上的不同取向,以及研究如何作为核心工作展开。OCAT深圳馆,自成立之初便将学术研究、展览、出版和公共教育作为机构工作的重点。保持对艺术家为个体单位的关注,OCAT过去十几年曾对谷文达、隋建国、王广义、张培力、汪建伟、舒群、徐坦等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文献整理工作,而隋建国的个展可以视为对这一项目的回归和延续。由崔灿灿策划的“体系”展览中,不仅展示了隋建国雕塑创作的过程和源起,伴随1400多张手稿,也将艺术家十年来所形成的创作体系的内在结构,通过如同长镜头般的展览现场,把十年的时间分割成不同的切面,以呈现出艺术家创作阶段的不同转向。
而广东时代美术馆在2018年策划了现居柏林的艺术家奥马尔·法斯特在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首次个展——“看不见的手”,并委托艺术家在广州创作拍摄了第一部虚拟现实(3D-VR)短片,进而通过影像挑战虚构与纪实的界限。作为美术馆“前景”项目中对处于职业中期艺术家的关注和支持,今年推出广州艺术家周滔的个展,将试图对电影这一媒介的叙事性提出挑战。周滔近年的创作都围绕具体的地点展开,这个被他称之为“地形”的研究,会如何围绕美术馆这一特定的空间和语境展开,仍然值得期待。
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作为由非营利空间转型的商业画廊,在前后十年的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美学线索和学术方向:对于当代艺术创作中尤其是从“85新潮”开始就贯穿至今的重要艺术家的个案研究,“蜂巢·生成”长期跟踪考察年轻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并为其举办个展和发行出版物。三月份在深圳的展览“虚拟语气”作为夏禹在蜂巢举办的第四次个展,延续了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对于青年艺术家的持续关注。作为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在深圳的南方分部,除了在学术性整体方向的外延,也试图为深圳,这个缺乏专业画廊的城市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可能:如何通过空间的展览与当地的艺术资源形成互补关系;如何面对深圳新兴的藏家群体进行培养和渗透;如何对尚在萌芽阶段的艺术市场进行普及和教育。
维他命艺术空间在2002年成立之初便试图通过另类空间的运作回应对于画廊和艺术机构的既有成见。维他命艺术空间最早位于广州美术学院附近一栋网吧后面的旧楼,回想笔者第一次如探险般找到空间,顺着楼梯、窗户和天花板的文字碎片行走,每一步拾阶而上都伴随一个疑问和思考:什么是大脑?什么是智力?……在搬至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农业大观园后,维他命艺术空间以一种更为日常且细腻的方式展开,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展览空间,而是一个承载并激发创造力的“田地”。以试图实现一种自治和有机的生产力。因此,一个普遍意义上观众的角色产生了变化,他将如同漫游者一般,在新辟的小径上、水流声中,感受空间、光线和所有在此发生的创造性的时刻。从去年冬天开始的“不确定任务”,人们受邀进入到这个日常的片刻,去理解艺术家田中功起从2012年开始,对于人类所经历的困境的思考。
>> 非营利机构的机构化之道 <<
现在的录像局和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以及本来画廊一起,位于泰康路的一栋历史保护建筑内,它们都由陈侗创办。成立录像局的初衷非常简单——建立一个可以观看艺术家录像作品的公共档案库。这个最早由陈侗、朱加、方璐发起的专门针对录像艺术的非营利机构,自2012年3月25日正式启动,设有北京和广州两处空间。他们保持着每年至少为12位艺术家建立档案的工作节奏,至今已收录83位艺术家约1800多件作品。2019年1月至3月展示的是最新收录的艺术家黄炳 (2010年至2018年)的20件录像作品和沈莘(2012至2018年)的12件录像作品。录像局的目的是明确的:为研究、学习和收藏的人群服务。因此,基于档案的建立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用并活化档案。录像局不定期举办录像艺术专题讲座活动,并在2017年策划出版了“录像艺术译丛”。此外,录像局还花费了两年时间研发自己的数据管理系统和视频点播系统。这一严谨的机构化运作,可以看到广东人特有的务实态度。
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2015年由杨锋先生在香港注册成立,旗下包括位于深圳的有空间、额外空间和上海的留下空间。作为创办者的杨锋经历了由艺术爱好者到艺术赞助人再到机构创办者的转变,因此在空间的定位上,除了作为一个标准的非营利空间,也试图成为一个“准公共机构”。它的对象更加明确:给予这个行业的艺术工作者一定的支持,其中就包含了年轻的策展人、艺术家和评论家等。而当我们提到“机构化”的同时,如何持续有效的运营,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给出了一种选择,蓝海资本作为主要的赞助人外,将展览、收藏和委任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生产机制以实现内部的稳健循环。在即将开始的“语言的窸窣”中,将得以看到空间精心挑选及委任的6位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对于现代语言在科技、人类和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的探索和转变。该项目与设计互联联合呈现。
录像局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运作方式,除却陈侗个人的出资行为,伴随近两年来市场经济活力的退减,为了更加持之有效地推动机构的发展和运作。录像局2016年加入了五行会,并在2018年成立自己的资助人计划,从2015年开始支持录像局的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成为了第一位理事机构。这一寻求联合及多元赞助的行动也直接指向了广州艺术生态中资本缺失带来的困境。2016年成立的“广州五行非营利艺术机构联合会”试图通过全面合作以促进广州当代艺术生态建设。五行会包括了广东时代美术馆、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录像局、黄边站和观察社。每年通过艺术家捐赠作品义拍的方式将资金回馈到机构来年的发展之中。这一做法看似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如何持之有效地推动这一机制,依旧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 设计之于设计之都 <<
八十年代以来借助香港外贸产业向珠三角的转移,从而带动了整个地区制造业、印刷业和广告业的发展。深圳从那时起经历了从“世界工厂”到“山寨之城”再到“设计之都”的转变。这种转变中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对于设计力和创造力的支持和鼓励。另一方面,介于主流之外的“无名输出”依然保留着(如中国最大电子市场的华强北和全球代工厂的富士康等)并持续作为城市在转型升级中的供起之源。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使得深圳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重塑人们对于制造和消费方式的认识。
设计的发展和它背后所推崇的理念息息相关。比如当我们提到瑞典,便联想到它的“民主化”设计,设计在强调“人”作为核心价值的同时,传递的是公民社会的美学意识,适度和平等的生活态度。设计在此成为一个完成政治和社会理念的工具,进而推演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那么当一座城市被推崇为“设计之都”的时候,设计之于社会的承诺是什么,又试图提供一种什么样理念和态度?华·美术馆在近几年的机构实践中可以看到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作为全国第一家设计美术馆,和OCAT深圳馆一样,都隶属于华侨城集团投资支持的OCAT美术馆群。美术馆除了保持对于视觉艺术的关注,也展开“理想社区生活方式”的探讨,进而回归设计对于“社会性”的关注。在华·美术馆的展览中,可以看到建筑师对于社群生活和理想社区的想象,“社会设计”和“社会实践”在国内的发展。当下正在展出的“01变量循环:缪晓春2006-2018”中,收录了十余组影像、动画、媒介和雕塑,除了是对艺术家阶段性成果的全面回顾,也呈现了艺术家通过数字技术虚拟构建的一个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世界。对于美术馆来说,如何通过展览和公共活动持续地激发当地的艺术生态,同时让公众能够积极的进入到美术馆所提供的社会实践和生活想象中,依旧是一个需要如园丁般持续开垦的工作。
一个城市设计力的发展,当然无法依靠一家机构的努力。深圳近几年来除了有各种规模的行业协会,也有大大小小的双年展,比如每年一届的深圳设计周、两年一届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深圳这个速度先行并高度城市化的社会现场进行回应。招商蛇口与V&A(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联合创办的设计互联|海上世界文化中心在蛇口的落地,通过其多元的展览、活动、演出与教育项目,展现设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是体现了深圳试图通过设计赋值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转型的雄心。设计互联旗下V&A展馆半常设展“设计的价值”通过近三百件展品,探讨“价值观”和“设计”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的价值观如何影响设计,而设计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一座城市的设计革新一定离不开设计理念和教育理念的并行,以及社会整体创造意识的教育和激发。作为一个创新文化综合平台的设计互联,如何将设计作为连接公众与文化消费、行业与产业研究的媒介,实现真正的互联、激发与创造,三者都很重要。
>> 不断加速的环形列车 <<
深圳现在是除了北京上海外艺术活动最活跃的城市,除了拥有一定比重的美术馆、各大双年展、深圳艺博会外,还能看到诸如TeamLab、游戏展及各种与新媒体有关的网红展览。深圳的艺术机构往往伴随着“社区”的总体营造,比如OCAT深圳馆所在的华侨城创意园区,经由对80年代留存下的工厂、仓库、宿舍楼进行改造,这个镶嵌在中产阶级住宅、欢乐谷、世界之窗的夹缝之地,在改造后不仅拥有一系列相互贯通的公共空间和设施,也吸引众多设计公司、画廊和艺术家的入驻,同时也变成当地文化生活的重要聚集地。随着整个城市的转型升级,越来越多大型的城市综合体应运而生。而艺术机构在此担任的角色也越发重要。但这中间也面临多重角力,在深圳这座有着不同肌理的城市中,如何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处理不同空间资源的问题和权利,艺术如何通过介入社会对现有的系统进行挑战。这其实都关乎着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和生活形态的想象,如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一切都在不断建立中。
反观广州这座城市,鲜有大型的艺术活动,艺术机构大都散落在城市的不同角落。每年最热闹的三月和十二月,也是借助香港巴塞尔和深圳艺博会期间聚集的人流。广州的艺术机构带有强烈的“自治”属性,如同广州的艺术实践一样,从九十年代起就注定了它“参与”的特性,一种主动的,面向现实的策略。它是极度政治性的,又带有一种“迂回的趣味”,其内在的抵抗意识和对日常生活的批判,直指“行动”本身。但是近几年来,由于长久以来资本的缺席,在面临市场经济不稳定和个人力量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机构也开始面临更多挑战。不管是时代美术馆新近成立的“藏家联合会”,2016发起的五行会,包括广州的第二代画廊(本来画廊和广州画廊)的发展也直接指向这一困境。表面看,“藏家”,这一广州大部分机构共同寻求的对象在当下无疑变得尤其重要。但更深层次体现的,是对更加健全的赞助人体系建立的迫切需求,是本地艺术生态对当代艺术系统的主动进入。也是当长久以来的“地方特色”开始失效之际,所有机构在当下不得不重新思考的严峻现实。
与深圳、广州不同的是,香港的艺术生态显然更具多样性。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国际化很大程度上来自市场和经济效益的推动。2018年香港接连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地标:基于古迹活化计划而开放的大馆、众多国际画廊入驻的H Queen’s大楼等。与此同时,去年九月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正式通车运营,从深圳福田前往香港西九龙站最快16分钟即可抵达,出站后便是正在建设的西九龙文化区,这一包含M+视觉文化博物馆、戏曲中心、艺术公园,并集艺术、教育及公共空间于一身的综合体正试图成为一张新的香港文化名片。伴随着基础交通建设带来身体的快速位移,人们对于距离的感知正被逐渐消解。这种便利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对于联结的构想蓝图。当我们回到这一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而发生的聚集时,在来到和去往之间,协同发展和互相联通对这特定区域划分上的艺术机构们意味着什么?如果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1982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坚立的标语牌,放置在被当代社会这辆不断加速的环形列车所挟裹的当下,跻身于列车上的我们,在这短暂的48小时的聚集后,下一站,又将去往城市的何方?
文/ 平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