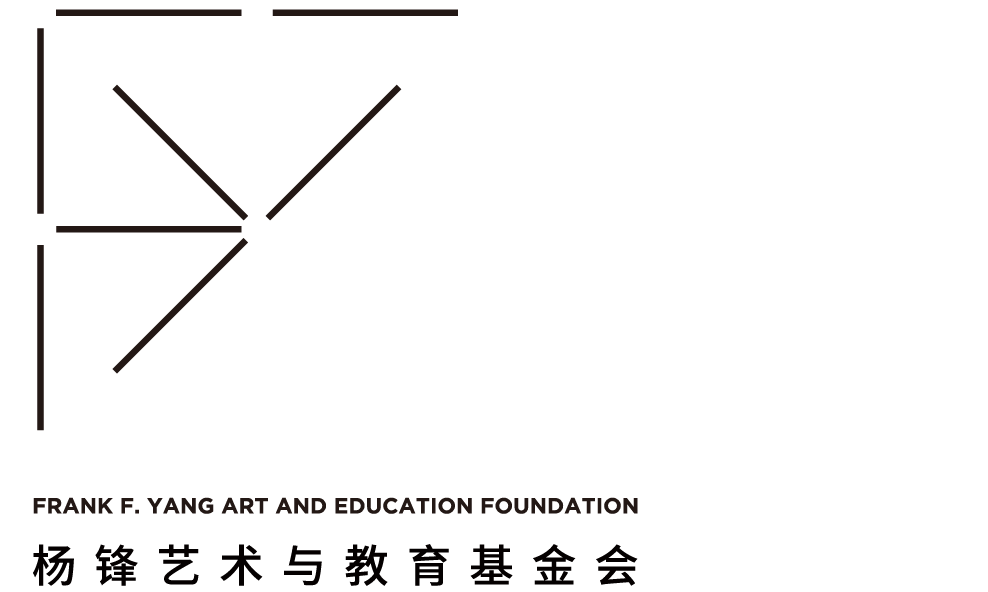在地性、文献及对话机制的构建 ——回顾留下空间的项目《当幕布拉起,我们的对话早已完结——留光显影》
汪单: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缘起:去年夏天,经朋友介绍,我们结识了杨锋艺术与教育基金会创始人杨锋先生。初次见面,杨先生和我、姜俊聊了很多有关留下空间的故事。留下空间经由几代房东转手,最终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栋房子才作为基金会的第三个空间。每一代房东都会保留一些前房东时期的室内装饰及花园的景,同时也依据个人的审美趣味,房东们对屋子做一定的改建。当时,杨先生也详细地介绍了留下空间的改建方案。园主、项目负责人和员工等参与到有关空间设计及施工方案的讨论,留下空间最终的样貌实则是一个集体讨论、协商后成果。
留下空间的历史和改建的故事启发了我们,带动我们去思考如何去挖掘空间本身的价值?从历史上看,留下空间的所在地“曲园”在上世纪中叶是一个高级定制的私人住宅小区。每一栋房子建筑风格都不同,空间的设计都是按照不同房主的喜好。曲园的历史及这块区域成为了我们这个项目研究的线索及素材。另外,我们这几年都在研究“在地性”这个议题和“协商”为先导的策展工作方式。我们期待这个项目能开启一种有别于白盒子空间的展览思路,包括跨学科讨论、文献推演,及艺术家将这些研究成果转译成作品。基于这个项目,我们了解和认识了一批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例如同济大学历史建筑研究的师生们,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研究上海历史的资深媒体人等。我们也将其做一个学术资源整合,创造了一系列对话和讨论。大部分展出的作品是基于上述的讨论和学术研究的分享,这也被视为一个集体协作的成果。不过,整个项目的筹备时间有限,展览还是有很多有待完善和深化的地方。
今天想聊的是,我不知道像这样的项目,涉及在地性讨论、文献挖掘及协作的工作方式,实则会碰到很多落地的问题,例如你在这个项目中如何有效运用你自己的知识,分享于他人,并最终能予以转化为富有创造力的作品。“鸡同鸭讲”往往是这类项目中的常见现象。
余玥:我认为当下的在地性艺术都会碰到这类问题。“在地性”其实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我们在古代时不会谈论“在地性”,但会谈论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本乡本土的问题。在以前的社会结构中间,“本乡本土”其实跟所谓的中央或者朝廷之间,有很强的转化机制,这种转换的做法实际上是不成系统的、慢慢的、交往性质。在古代还没有一个彻底自支撑的系统,甚至连朝廷都不是系统性的和完完全全的组织性的,比如说像姜俊以前比较喜欢的那本书《叫魂》,就展现了复杂的朝野关系成型之中的状况。
但我们今日的“在地性”,它的的确确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化了的并且系统化了的对手,这个对手就叫做“全球化”,或者可以叫做普世化,或者也可以把它叫做全球的资本主义化等等,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描绘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地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困难,就是“在地性”如何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现有的普世性的话语其实是非常强大的,而你是不是要去造一个非常强大的话语系统,以对抗另外一个强大的话语系统?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实就是想把民族的表达方式和语言、文化普世化。也就是说,你是要用另外一种普世化去代替现有的普世化。这不过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普世化而已。
那在地性还可以应该做什么事情?如果它脱离系统,完完全全的零散化,仅仅停留于某些特色的表现。那其实是一件非常无力的事情。那些散碎的片段会被整合到普世化的进程之中,或者直接被抛弃,正如我们这几十年来城市化的建设,其整个作用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即在普世化的立场上,是一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做法。这种方法就是一种取舍:对于整个普世化建设来说有作用的东西就将它保留下来,把它转变为普世化的言说框架内处理的对象,反之就丢掉。所以在地性的工作是要把那些所谓的“糟粕”拿来展示一番吗?显然这也不是在地性工作真正要做的。
我看了留下空间的展览,知晓了项目背后的一系列工作,我觉得项目本身还是很有意义的。我可能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自我成型中的一种非体系的、但是可以借用各种资源的一个协商空间,我会把它称之为一个对话的场域。也就是说,事实上“在地性”今日要做的工作,第一并不是要再造另一种普世系统,第二也不是说要把普世系统所抛弃的那些东西简单地重新拣起来。“在地性”在与普世化对抗的过程中,体现为对以下问题的意识,即:对于某种已经被打裂了的东西,已经被切断的东西——这个被打裂和切断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所造成的那种我们今日生活和之前生活间的断裂,这个断裂在各种层面都可以看得到——如何可能在特定的一个平台上面重新被讨论。至于说讨论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可能需要再假以时日来验证,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讨论就是你们想要去做的。而我觉得,即使在整个当代艺术中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它也就是所谓的当代艺术的居间性,即让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特定时空场域中重新被讨论,并且重新保有它的可能性的那种特性。我现在说的这一点跟跨学科还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完全可以是艺术家内部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今日在地性的工作如果继续在你们现在做的那个方向努力,可能是有前途的,它完全不同于前面两种在地性理解。
汪单:当下,所谓的“活化文献”像是一个当代艺术发展的潮流,全球的机构和当代艺术从业者都在讨论这类问题。很多人也认同文献挖掘作为一种当代艺术的创作方法,也寄希望于艺术家最终能将文献的价值转译、再现。但是,我不确认最终这类项目“点石成金”者是归功于艺术家还是文献挖掘、研究的工作者?
余玥:你刚才说的涉及到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活化文献的层面;第二个是在过程中间艺术家的角色问题。我首先说说我有比较成熟看法的第一点,然后再转到艺术家方面来谈。
我觉得活化文献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个词也是用得非常好。我们首先要知道:所谓的档案和文献是在什么意义上被建立起来的,然后才可能大概知道我们今天做的工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现代之前也是有文献的,这些文献主要是为了传承某些永恒的或者有价值的事物,典型的例子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他说这本书现在没有人读也无所谓,我可以让它“藏之深山,留之后世”,就是说把它藏到山里头,然后留到后面有人的时候再来看它。事实上,能够成为文献的,就是这些具有跨时空的意义的东西。再比如一直以来,中国都有一个传统,就是不要轻易写文章,否则就容易“颇悔少作”,就是很后悔以前写过这些东西。在这个情况下,人们可能要等待一个相对长的时期,才把真正要写的东西写下来,这就是所谓定本、定稿,这些东西对于整个古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都是具有跨时空的永恒价值的东西。
到了近代之后,文献或者说档案的角色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换。它涉及到整个近代世界整体化的趋势,比如说像潮汐、水文、气温,或者地理、事件空间,或者社会的各个阶层,对之加以记录的档案就是对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且十分有用的内容。为什么这些东西是非常有作用的呢?因为,近代社会之后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细节极其丰富的世界。如果依据以前那种精英化的文件保存及写作方式,对处理这样的世界来说实际上是不够的,大量细节性的那些文件需要被补充进来,其目的就是可以基于这样一些文献,提取出某些所谓的科学规律或者是管理的方法,或者是让社会可以在整理大量的文献档案的基础上便捷地去行事。
总而言之,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控制,文献的掌握逐渐形成了对社会的整体见解,以及能够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某种控制。这个发展到今天也是令人担忧的事情,比如我们会担心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可能结果,就是一个控制型社会的指数级成长,甚至以后可能小孩子出生后,就可以通过他的父母亲戚的档案,以及他的居住环境等等一系列的档案、信息,把他判定为有多少的几率会变成一个坏人或者好人,然后基于此对他进行教育和管理。对基于海量档案的控制性的、预测性社会的担心,是目前普遍存在着的一种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活化文献”就成为一个问题。在我的理解中,“活化文献”所相对的那个“死”的文献,其实不是说没有被利用的文献,而是说被利用来去塑造一个自控制的、自升级系统的社会文献。活化文献的工作重点在于:我们要去寻找到一种有主动性的空间,一种非完全控制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种,可以生成自主的文化记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机构或是创作者都从事于档案的整理工作,但仅限于一个简单的记录工作,就是把曾经被忽略的东西收集并展示出来,或者用一些艺术的方式把它转化为相应的视觉形象,以此强调这些不应被遗忘的信息。这些工作都是有价值的,但我也怀疑,仅仅在这样的工作中能否找到与我们的主动性相关的的文化。大部分在地性的作品里也存在这个问题。
我再谈一下艺术家的角色。今天,在地艺术家也会存在着一个很麻烦的身份问题,就是他们创作的作品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称之为艺术?这也回到我刚刚提及文献的整理工作。如果我们仅仅整理几十年来上海某个社区发展的文献,或者是参与到整个社区变迁的进程之中,并且留下痕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工作还不能够被称之为活化文献。它们要么是被现代化淘汰后所留下来的文献,但未被界定其价值。要么它也可能是一份有用的文献,并且可以被收入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并服务于整个科研体系,也就是说,科研系统可以通过这些文献更好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下一步要去怎么做。以上这两种方式都不是活化文献的工作。同时,它也并不属于真正可以称之为艺术家的工作。在现代之后,艺术家创造性的身份得到了非常高的重视,但是在地问题不仅是简单的创造问题,它实际上是说:我们必须要有控制型现代社会之中的某种主动性,并且这些拥有主动性的人要在拥有自己的特定时空下的文化记忆的同时,形成新的、具有特质的文化记忆,他必须思考:在这个过程里面,艺术家可以做什么?只有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在做活化文献工作的人。
这也让我觉得 “留下空间”项目是有趣的。整个项目强调艺术家必须要理解文化记忆的内涵,并且转换为一种新的语言,使得那些新的文化记忆产生效果,这两部分缺一不可。因此,艺术家必定要以某种理解者、组织者、翻译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个显然与凭灵感创作的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也很大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会把参与到整个进程中的人都称之为艺术家。他们可以带着各自的理解和自身的学科背景,加入到这样的工作团队中间。参与者并不是借项目来服务于他的学术建设,或者仅仅是满足自己的某种乡愁。我所期待的,以及我在这个项目中看到的,是一种新型的艺术家,他们会做某些策展人的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也同时也在做转换某些传统的创造性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团队的人,也不简单是一个跨学科交流活动的从业人员,这些人员的工作方式是:我有我的学科见解,你有你的学科见解,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事情,就这个事情我提取我要的成分,你提取你要的成分,然后这件事情就可以到此结束。相反,在今天整个当代艺术中间,(依据文化记忆生成文化记忆)这件事情越来越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大致澄清了心目中可以被称之为跨学科的意义。
我们曾经探讨过,当代艺术以前是以反叛的、革命的和批判性这样的态度为支撑和依据,但当代艺术走到今天,反叛或者批评已经成为一个传统,它必定要面对一个如何在反叛、批评之后做什么的问题。而我觉得在地性艺术可能就是在批判之后开展工作的一种方式。
汪单:非常感谢余老师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我们可以继续推进工作。
| 作者 |
汪单,ePublicArt(电子版公共艺术杂志)主编,国际公共艺术协会研究员、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展览项目部助理总监。2011年毕业于伦敦大学Goldsmiths 策展专业,获艺术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人物专业,获本科学位。2011年8月到2013年4月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展览教育组,主要负责展览协助及教育活动策划。2016年获得吴作人基金会与卡蒂斯特基金会合作“青年策展人奖学金”。
余玥,四川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德国波鸿大学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心暨黑格尔档案馆,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现代性问题、实践哲学及美学。